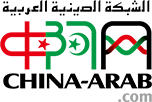“伊斯兰国”走向后巴格达迪时代
近日,伊拉克摩苏尔,伊拉克联邦警察成员庆祝摩苏尔战争胜利。(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
巴格达迪是否确已毙命,某种意义上已并非核心问题。重要的是,作为统一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地理政治实体的“伊斯兰国”,目前基本丧失了继续维持的可能。
按照民族分布和历史、文化传统重构中东国界的理想,自20世纪初以来始终是本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伊斯兰国”覆亡的同时,新的国界和势力版图也已在酝酿之中。
三年里第N次,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被击毙的消息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地带传出。只是这一回,各国政府和新闻媒体都不曾大肆渲染。这个人是否确已离世,目前已不再是核心问题,人们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关心:摩苏尔解放之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控制的领土就只剩下尼尼微省和萨拉赫丁省两块不相连的孤立占领区,以及安巴尔省的干旱草原与沙漠;在叙利亚,他们占据的霍姆斯省东北部和代尔祖尔省大部同样为广袤的沙漠无人区所覆盖,经济、军事价值微乎其微。这个活跃于全球媒体头条已有三年半之久的恐怖主义团体,即将丧失其赖以逞凶的基本根据地。
与“基地”组织乃至此前其他声名在外的恐怖主义团体相比,“伊斯兰国”最突出的“新意”,在于其试图恢复消失已有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哈里发”制度,首先在黎凡特地区建立政教合一的主根据地,继而唤起全球潜在支持者的效忠。2014年以来由“伊斯兰国”主导的恐怖主义活动,大体也遵循根据地经营与分散式袭击并重的路线。随着“伊斯兰国”主根据地接近被消灭,未来一段时期内,由极端宗教思想驱动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将再度回归相对分散的模式。
但对中东世界而言,“公敌”的崩溃,却可能成为催生新的部落化趋势的起点。以民族为中心重构中东政治版图的可能性,即将迎来最近一百年里的第N次复苏。
竞争者“哈里发国”
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中东政治现代化,本质上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相互竞争。在基于国家主义的努力相继偃旗息鼓之后,带有复古色彩的“哈里发国”的回归遂也顺理成章。
自2014年“伊斯兰国”将其暴恐袭击的重点指向西欧,从而引发全球舆论的关注以来,政治学者一直试图梳理“黑旗”背后的宗教和历史逻辑。
2015年春天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长文《“伊斯兰国”到底要什么?》,一度被认为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篇。但即使是这篇文章,也过于高估了“伊斯兰国”的实际政治运作与其宣称的宗教理念之间的关联程度。20世纪以来的中东政治变革进程,始终是理论适应实际的结果;其每一关键节点的出现和轨迹的嬗变,几乎都受到当时国际格局的直接影响和诱导。
1916年领导阿拉伯半岛各民族起义的,是身兼部落首领和穆罕默德后裔双重角色的哈希姆家族成员;最早推动巴勒斯坦自治和建国运动的,则是出身侯赛尼家族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教法释读官)。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于现实需要,力促阿拉伯各部落领袖投身反对土耳其的军事斗争时,也把这种尚未发育成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早早推向了实践。而当英法两国在战后直接否决了建立“从阿勒颇到亚丁”的单一阿拉伯国家的可能性之后,本身分歧众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内部竞争:哪一派别能完成一统中东世界的伟业,哪一派就能拥有最大程度的正当性。
从1920年哈希姆家族创建的“大叙利亚王国”,到纳赛尔及其追随者的阿拉伯社会主义,20世纪中东历史上最重要的几次政治变化,本质上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中那些从未形成合力的早熟因子之间的碰撞。
独立初期的伊拉克和约旦尝试过部落制与英式君主立宪的混合,沙特王国用石油财富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巩固其瓦哈比派教义,纳赛尔试图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社会控制扬弃旧有的国界,复兴党领导下的伊拉克与叙利亚则力图建设单一国家内的强人政体。
每一种尝试,又都以外部世界的动荡和秩序重构作为契机——由于掌握着至关重要的能源命脉,“一战”以后世界秩序的每一次转换,在中东都能立即触发风向的改变和政治潮流的洗牌。而中东世界的政治动荡和权势倾轧,同样在改变着现代世界:1979年之后,正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失意者的集体东行造就了结出无数宗教极端主义恶果的“阿富汗熔炉”。
只有从派别竞争和全球大势演变的角度,方能解释以“哈里发国”模式作为标榜的“伊斯兰国”诞生的政治逻辑。21世纪初的中东危机,本质上是国家主义的全面失败:以伊拉克为代表的强人政体在美国强横的单边主义干涉下迅速倾颓;全球化普及进程的不均衡,则使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的底层民众高度怀疑其威权领导人统治模式的可持续性。动荡的“阿拉伯之春”,在摧毁了以准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旧秩序之后,势必要寻求新的出路。
而“伊斯兰国”恰恰对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在根据地上,它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联系素来密切的阿拉伯半岛北部,并且恰恰对应100年前第一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图建立的“大叙利亚”的大致版图。在“建国”模式上,它回到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多民族治理,呼吁基于宗教认同,向“哈里发”巴格达迪效忠,同时力图取消现有的中东国界和分立的各国政府。在纲领上,它试图以古老的宗教法典对抗驳杂多元的现代主义,从而将历史时针重新拨回到了20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早熟期。
“伊斯兰国”,终于从民族国家的废墟上崛起。
三年里第N次,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被击毙的消息从叙利亚和伊拉克交界地带传出。(视觉中国/图)
机缘巧合的猖獗
国家主义失败的“大气候”,与伊拉克、叙利亚两国政府治理失能的“小气候”形成合力,开启了属于“伊斯兰国”的时间窗。但随着美俄在反恐力量上的加大投入,猖獗并没有维持太久。
在“伊斯兰国”不长的崛起历程中,有两个关键时间点需要被记住:2010年,该团体前身之一、“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在美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打击下,已经退居北部极少数不相连的控制区。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撤出在伊拉克的美军战斗部队,并在2011年底之前完成全部撤军。2014年,随着叙利亚内战进入新高潮,主要由AQI人员组成的“努斯拉阵线”武装从叙利亚北部向伊拉克境内反攻,并于当年6月29日宣布“建国”。在这期间的某一天,伊拉克人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决定改名为“巴格达迪”,并以黑袍、黑头巾、蓄须的造型出现在摩苏尔著名的地标努里大清真寺的院落内。
发端于伊拉克,在混乱中的叙利亚获得壮大的机会,最终通过反攻伊拉克达到领土和人口范围的顶点:这是“伊斯兰国”前期的成长轨迹。巴格达迪对当地时局的洞察,于此可见一斑。到2010年夏天为止,AQI不过是活跃于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数十股反政府武装之一,其重要的军事、政治领导人在美军的围剿下屡遭击毙,残余势力已经难成气候。小字辈巴格达迪决定率精干军事人员“西征”,进入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叙利亚北部。
2016年秋天,笔者曾在伊叙边境线东南方的安巴尔省做实地探访,在当地逊尼派教众眼中,国界从未割裂他们与叙利亚中北部的代尔祖尔、拉卡、阿勒颇三省基于商业、文化往来和信仰一致形成的亲缘关系,民族差异的区隔远未成为自觉的身份认知。而代尔祖尔、拉卡和阿勒颇正是2010~2014年间巴格达迪及其“努斯拉阵线”扩充兵员、经营经济和人口控制范围的核心根据地。
与此同时,在伊拉克,什叶派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政府已经与盘踞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逊尼派民兵团体彻底决裂,并开始了事实上的内战。大批接受过美军训练、使用美制武器,原定要从事反恐行动的军人转而开始对抗伊拉克政府,其中不乏具备阵地战经验的前萨达姆军队高级将领。曾任“伊斯兰国”军事领导人的阿布·阿里·安巴里,便曾是萨达姆“共和国卫队”的一名少将。而“努斯拉阵线”趁机与这批反政府武装结成一伙,并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开始经营独立团体“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2014年6月,该组织全面进攻伊拉克北部,接连攻陷摩苏尔、提克里特、拜伊吉等重要城市,并于当月底正式宣布成立“哈里发国”。
如果说昔日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采取的是与塔利班政权相互利用的政策,那么“伊斯兰国”在其曾经的控制区奉行的就是一种准国家化的恐怖主义。巅峰时期,“伊斯兰国”武装控制叙利亚60%的石油开采设备以及伊拉克10%的油田,日产原油约20万桶,其中有1/3经黑市走私到土耳其,每日可创造200万美元的进账。以这笔收入以及在占领区征收的税款、绑架人质的赎金作为凭靠,巴格达迪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新兵,并鼓动和资助追随者从事规模不等的暴恐袭击活动。
而巴格达迪对“哈里发”名义的僭用,使得西至利比亚、东到菲律宾、南达也门的宗教极端分子,突然有了统一的效忠对象。是以“伊斯兰国”在“建国”后的前两年,接连在西欧制造多起针对平民的袭击,一跃而超过“基地”组织、成为全球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团伙。
然而,时过境迁,因国家失败而崛起的“伊斯兰国”,也将在国家力量的复苏面前迅速衰败。进入2016年,随着俄罗斯和伊朗强势介入叙利亚,叙利亚得以确保对西部经济-人口核心区的控制,稳定住了战线。在伊拉克,安全部队与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联手发动北伐,向摩苏尔周边步步紧逼。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显示了除大规模出兵以外最大的介入力度:支持一切愿意参与对“伊斯兰国”战斗的武装团体,集中力量围剿后者的核心控制区。被“建国”的虚名固定在主根据地上的“伊斯兰国”,日渐丧失其经济和人口来源,终于由盛转衰。对其主要控制区的收复行动,有望在2017年内完全结束。
难灭的“大国”余烬
政教一体的野心破灭之后,重新被唤起的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依然会继续投入重构国界和政治版图的斗争。“大叙利亚”“大库尔德斯坦”“什叶派新月”,每一个方案都拥有更根深蒂固的心理以及现实基础。
“伊斯兰国”的覆灭以及重新走向游击化,几乎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它在叙利亚-伊拉克交界地带的勃兴,恰恰对应了“一战”结束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统一的“北方之国”或“大叙利亚”的政治想象。
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到纳赛尔主义兴起,从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建立到老阿萨德入侵黎巴嫩,中东世界的每一波政治格局重构,几乎都会伴随有“大叙利亚”理想的某种变体的再起。大叙利亚之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已成为信仰一般的存在。这个从未在地图上出现的“国家”,同样是现代阿拉伯政治的某种投射,其阴影在未来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另一个因叙利亚内战和“伊斯兰国”兴起而获得再生的地理概念,则是“大库尔德斯坦”。“一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曾承诺允许库尔德人独立建国。但随着土耳其独立战争的胜利,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大库尔德斯坦最终被分割到了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四国领土之内,其独立意愿则屡次被强势的国家主义领袖所镇压。
但一切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发生了变化:聚集于杜胡克、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三省(即南库尔德斯坦)的五百余万伊拉克库尔德人再度揭竿而起,完全控制了这片7.8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起自己的议会、政府和独立的武装力量。在2014年以来对“伊斯兰国”的作战中,南库尔德“决死军”基本以自筹军饷和武装、独立行动的方式作战,并不听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指挥。
如此振奋人心的前景,自然会为叙利亚境内的西库尔德人所效仿。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西库尔德斯坦4省的两百多万居民在“决死军”的援助下,驱逐了忠于巴沙尔政权的部队,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宣布组建独立的自治政府,并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2016年12月,该政府正式更名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其武装部队更名为“叙利亚民主军”,开始寻求更大限度的独立。
尽管大马士革当局从未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但由于“民主军”在对“伊斯兰国”的作战中表现活跃,从美国到俄罗斯在内的主流国家皆承认其准独立地位,伊朗也在通过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对北部联邦施加影响。而西、南两块库尔德斯坦自治领土在事实上已经连成一体,一面从事与“伊斯兰国”的战争,一面吸引土耳其境内的北库尔德人来投。正如对“大叙利亚”的想象在不同时期曾经成为一统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历史凭据,当“大库尔德斯坦”的理想在21世纪被重新激活之后,短期内也绝无偃旗息鼓的可能。
从“大叙利亚”到“大库尔德斯坦”,再到伊朗扶植下的从约旦延伸到也门的“什叶派新月”,都因叙利亚战争而被唤醒。在“伊斯兰国”这个公敌被最终消灭之前,各派尚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合作和共识。但一旦共同的打击目标不复存在,“大国”的幽灵们将在新月沃土之地正面遭遇。届时出现的将很难是稳定的和平,而更有可能是一种部落化的分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