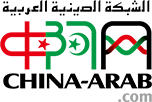东盟—海合会经贸合作及其对中阿经贸合作的启示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分别是东亚地区和中东地区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组织,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从政治和安全组织向经济组织拓展。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东盟整合了10个成员国的经贸发展,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是推进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海合会则协调了6个海湾石油君主国的发展步伐,两个地区组织对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区域经贸合作的角度来看,东盟以集体的名义与中日韩3国建立了“东盟10+3”的机制,该机制涉及发展与合作等议题,覆盖了绝大部分东亚国家(朝鲜除外),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也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不仅如此,东盟6个成员国还参与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成为连接东亚、大洋洲以及美洲国家经贸合作关系的核心国家;海合会一方面与中东其他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地中海沿岸中东国家加强早已有之的经贸联系,在欧盟—地中海合作框架以及建立欧地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之下,海合会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也在断断续续谈判之中,海合会对于连接地中海沿岸中东马格里布国家和黎凡特国家以及欧盟国家也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东盟与海合会近年来经贸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成为连接世界经济以及各自由贸易区的有力推进。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第三世界国家南南合作的典范,对于传统的依附论、“中心—外围”论等是一种突破。
一、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由来与现状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一定数量的投资活动越来越明显。1986年,海合会部长会议第18次会议同意与远东国家尤其是东盟和韩国建立初步的接触。但1990年以前,东盟与海合会没有建立官方的接触机制,主要通过联合国大会的管道而进行临时性会晤,其合作极为有限。1990年以来,东盟与海合会建立了日常的联系机制,但两个组织内部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缓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入以及官方联系的层次。尽管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于1992年建立,但东盟本身也在扩大过程之中直至1999年柬埔寨加入才宣告完成,而海合会直至2003年才建立海合会关税同盟,2008年启动海湾共同市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从海合会到南亚与东盟的资本流动包括建立在非正式双边及官方的多边基础上的汇款、财政援助与发展援助,银行间交易以及高净值公民个人的组合投资。”[1]
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突破出现在2000年2月,海合会总谈判协调员访问东盟总部并会见了东盟秘书长,双方探讨了海合会国家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前景。作为回访,由部分东盟国家驻沙特大使组成的东盟委员会访问了海合会总秘书处,双方讨论了经济合作等方面的问题。2007年4月21日,东盟秘书长王景荣与海合会秘书长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蒂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会谈,该会谈涉及双方共同关注的地区与国际问题,王景荣强调:“我们寻求推进秘书处对秘书处级别的合作。东盟正与海合会一道开发不同部门的合作方式。”[2]2008年7月,东盟国家外长第41次会议决定谋求海合会国家外长同意建立一种年度外长会议为形式的正规化机制,海合会对此作了积极回应。2008年9月,东盟秘书长素林·披素旺访问海合会时在沙特指出:“随着世界范围内油价的上涨以及对于粮食短缺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东盟与海合会形成共识,即可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以及有关这两个地区问题的更紧密地协调”,海合会秘书长阿蒂亚指出:“我看到我们东盟—海合会增强的合作中有大量潜力”[3]。在东盟与海合会约定来年的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2008年8月21日,海合会国家政府间商贸组织“海湾国家商工联合会”(FGCCC)以及“国际海合会贸易中心”在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MIDA)设立“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GAEC),该中心作为这两个机构“唯一的官方代表机构”,不仅如此,它还“从海合会获得必要的支持”。“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的宗旨在于:1. “加强海合会与东盟成员国之间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2. “引导一切在以下领域建立联合企业和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石油与天然气;贸易;金融(银行、投资、保险);食品与农业;房地产;教育;其他(如信息技术、旅游等)”;3. “扮演这两个地区国家间催化剂和桥梁的角色”;4. “通过明确的机会和采用共同利益的合资企业去创造经济与社会活动所有领域的思想与计划,以增强这两个地区国家间经济活动的发展。”[4]从具体合作的服务对象来看,主要针对东盟与海合会国家中在“海合会—东盟经济中心”注册的政府机构、政府有关的公司、私营公司以及商人;从服务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招标分配;组织相关政府机构与公司间的会议;建立商业配对和网络计划的伙伴关系;进行可行性研究;介绍促进合同谈判的解决方案;法律、文秘和会计服务;进出口及清关服务;为酒店、餐厅和机票提供特价优惠安排;进入海合会的签证与入境许可;为协商与会议提供的指导方案和翻译服务;为成员及其雇员在获认证机构开展研讨会与训练计划;访问所有注册成员及其活动的数据库;通讯与公告服务;海合会与东盟当地市场、规则和法规的信息。[5]
正是在长期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框架的基础之上,东盟与海合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便水到渠成。2009年6月29至30日,首届东盟—海合会部长级会议在巴林举行,东盟与海合会国家部长、高级代表以及双方秘书长出席,旨在“发展更紧密和更有益的关系”,目标在于“建立东盟—海合会合作框架及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促进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旅游业”,东盟与海合会互派大使也提上了议事日程。[6]在《联合声明》中,双方“强调了依据国际法打击海盗的重要性”,“认识到贸易和投资的潜力”,“强调两个地区的私营部门通过促进东盟—海合会商业论坛来紧密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食品安全及发展农业生产、供应和食品标准领域—包括清真食物产品—合资企业的重要性”,“注意到在能源部门,包括烃能源和可替代、可再生能源信息交换方面合作的潜力”,“表达了对当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关注并认识到对双方不可避免的影响”,“同意建立官方网络以及旅游相关活动的推进和规划”,双方还约定签署《海合会—东盟2年工作计划》,并决定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于2010年在东盟国家举行。[7]东盟对深化与海合会的合作表现积极,2009年12月,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商务部长彭提娃·纳卡塞会见阿联酋代表时指出:“对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已基本完成。如果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协定(FTA)将对双方产生积极后果,那么双方应同意尽早开始谈判。”[8]2010年2月28日,第16届东盟经济部长务虚会主席伍辉煌指出:“部长们鼓励官员和东盟秘书处组织与海合会的圆桌讨论,并呼吁他们对可能的领域和地区参与机制集思广益。”[9]2010年4月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在沙特协商会议发表演讲时指出:“亚洲国家依靠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地区来确保其能源需求,而海湾国家正瞄准食品进口与投资农田以确保其战略食品供应”,“你们拥有我们所没有的,而我们拥有大量你们所没有的,因此我们必须携起手来”[10]。2010年5月16日,由柬埔寨和科威特主持的东盟—海合会会议在利雅得举行,该会议审阅了2010至2012年行动计划,并讨论了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议程等。
二、东盟与海合会经贸合作关系的特点
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关系基于共同的成熟的地区经贸一体化实践以及“经贸促和平”的自由主义理念,经过数十年渐进式的接触与磨合,已逐步成形。具体而言,从合作的主导者、合作的领域、合作的方式等方面来看,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是小国联合自强主导彼此间合作的典范,其双边合作涉及油气资源、农产品等,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在此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特点,即东盟与海合会间双边关系为引导,东盟具体国家和海合会具体国家的多管道合作为基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谈判为终极目标,东盟具体国家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为先行。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参与全球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层次不一,由低到高可分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货币与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而最常见的形式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是“通过一组国家为消除它们之间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商品的贸易壁垒而建立”,“通常是地区性的,出于地缘的考虑”,“也可出现在彼此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不一定让各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的关税整齐划一。”[11]东盟业已建立起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海合会也建立起发展层次更高的海湾共同市场,并正在向货币与经济联盟迈进。建立与其他地区组织或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和海合会的现实选择。2010年元旦建成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是东盟参与建成的首个自由贸易区,而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和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建成,东盟与印度、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与东北亚、南亚及大洋洲主要邻国建成或即将建成自由贸易区之际,东盟呈西进态势。海合会则与中国和欧盟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难看出,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目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而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东亚的中国,除中国国外,双方的对象国不尽相同,因此,东盟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连接东南亚和中东,甚至促进欧亚非的自由贸易极有裨益。2009年12月世贸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东盟轮值主席国泰国的商业部长纳卡塞(Porntiva Nakasai)与阿联酋的代表讨论了东盟与海合会之间贸易自由化的问题,纳卡塞指出:“对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研究基本完成。双方应同意尽快开始谈判,假如它们发现自由贸易区将为彼此创造一个积极的结果,”她还指出,阿联酋支持尽快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12]2010年4月11日,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家主席阮明哲呼吁在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尽力“建立自由贸易区”。尽管东盟与海合会自由贸易区尚未建立,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优势互补,东盟存在着与具体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而海合会有着与地区组织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经验积累,这对于这两个地区组织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会有极大的帮助。
东盟与海合会之间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是双方领导人的共同追求,但双方也明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不能一蹴而就。在东盟—海合会自由贸易区作为终极目标的前提下,东盟一些具体国家已与海合会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或正在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整个东盟国家的先导。2006年11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访问沙特期间正式与海合会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问题,2008年12月15日,新加坡正式与海合会在多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GSFTA),这是海合会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涉及商品贸易、投资、劳务人员流动、海关手续和政府采购等多个领域,但具体细节仍待海合会成员国逐一修改后确定。新加坡外长杨文荣2010年3月访问迪拜时与海合会有关国家政府官员确定,新加坡—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将在2010年晚些时候正式实施。杨文荣的访问不仅是为了2010年5月底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东盟—海合会部长级会谈作准备,其具体目标还在于推进东盟与海合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展,杨文荣指出:“事实上,新加坡所期待的将不仅仅是新加坡与海合会之间的未来的协定,而是东盟与海合会(之间也将有此协定)”[13]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首个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并非偶然,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度等息息相关,新加坡是东盟十国中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2009年下半年,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的启发下,开始萌生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想法,2010年3月,马来西亚正式表示愿与海合会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部长穆斯塔法指出:“我们认为与海合会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进一步增强马来西亚与该地区商业机构间的联系确有必要”,“马来西亚已与海合会秘书处进行了交谈,但严肃的谈判迄今尚未开启”[14]。尽管马来西亚将伊斯兰金融等作为其与海合会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只有阿联酋明确表态支持马来西亚—海合会自由贸易区。由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就许多具体国家而言,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十分艰难,但诸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努力对于东盟与海合会未来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应该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其次,东盟与海合会之间分别以油气资源和农产品为最为迫切的需求,这构成了双边贸易的主导,而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多渠道、多领域经贸往来则构成辅助性经贸合作方式。
就东盟与海合会主导的粮食换石油贸易而言,这两种贸易商品皆非普通意义上的贸易品,而是具有战略和安全意义的特殊商品。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命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粮食的自给自足或稳定粮食来源的确保,不仅如此,粮价的波动对于产粮国和粮食需求国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和连锁反应,“国际社会对粮价上涨的密切关注和担忧揭示了粮食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和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任何关键性的因素波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问题便是其一。”[15]海湾阿拉伯国家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而深刻感受到粮食安全的紧迫性,这种不安全感会诱发以下问题:“引发社会群体心理不安,破坏社会稳定基础”,“引发社会冲突,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政治依附性增强,国际话语权受制”[16]。海合会国家除沙特外多为小国,国土内多为沙漠地带,可耕地面积较少,这是农业的先天不足;水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大量增长对于农业的发展以及粮食安全是致命的冲击,“该地区可利用的纯净水资源低于全球可利用纯净水资源的1%”,“然而,该地区是世界5%的人口的家”,“海合会总体人口增长率——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在1990年至2009年之间为3%。”[17]海合会国家与以色列的地理状况极为类似,但出于对以色列的不信任感而未将学习以色列的先进农业技术作为首选,而是利用其丰富的石油美元在全世界购买粮食以分化粮食安全风险,东盟国家因所处地理位置而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而成为海合会国家购买粮食的重要地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并向全球拓展以及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布局,新兴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离不开石油。尽管东盟国家如越南、印尼等也有一定的油气产量,但远远不够东盟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争端对于其目前的石油产品生产具有潜在与现实的威胁。而海合会国家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无论是美欧还是中日韩都在此角力,就东盟各具体国家而言,与这些大国在海湾地区的竞争毫无优势,以东盟的身份与海合会加强油气贸易成为首选。2009年3月1日,新《东盟石油安全协议》(APSA)正式取代1986年的旧协议,其核心内容在于维护东盟石油资源的独立性。正是在东盟与海合会各具优势且需求互补的前提下,双方加强了在农业和石油贸易方面的合作。2009年6月东盟与海合会首次部长级会议中便有石油换粮食的计划,海合会便打算从进口粮食变为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农业生产以实现双赢。“亚洲国家依赖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地区以确保它们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在瞄准粮食进口与农田投资以确保它们的战略粮食供应”,泰国外长甲西·披龙耶的话表明了东盟的立场:“我们可以保证海湾地区未来十年任何数量的大米消费。”[18]
在东盟与海合会最为迫切的粮食与石油贸易紧锣密鼓筹划之时,东盟国家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多领域双边贸易正如火如荼展开。缅甸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农业贸易便极为成型:2008年8月,缅甸与科威特签署贸易和投资协定,旨在促进科威特投资缅甸农业;2009年9月,缅甸与阿联酋迪拜贸易促进会(DMCC)谈判关于缅甸向阿联酋出口10万吨大米事宜。越南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其20余年革新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对海湾出口包括粮食、生活用品以及工业品之外,还包括劳务输出。截至2008年,越南在中东的劳工有约21000人,其中卡塔尔10000人,阿联酋9000人,沙特2000人;不仅如此,卡塔尔还与越南签署协定,将2008年吸收越南劳工的数量扩大至20000人,今后数量逐年增加。[19]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近年频繁,海湾国家商工联合会秘书长纳奇2009年6月访问菲律宾与阿罗约总统会见后指出:“阿罗约总统在我们的会议中表明了她扩展与海合会在所有领域,尤其是贸易、投资和劳动力部门合作的愿望。”[20]具体体现在:菲律宾与海合会国家私企之间的双边合作正在扩大;海合会通过合作公司的形式投资菲律宾农业,尤其是建立合资企业生产清真食品以出口海合会国家;海合会增加对高素质菲律宾劳工的吸收,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熟练技师。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这与海合会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在全世界穆斯林国家之中,海合会国家近年来成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与海合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自1999年以来开始增长,2003年达到30亿美元,2006年为80亿美元,其中70%的双边贸易额来自沙特和阿联酋。[21]马来西亚侧重于几个方面的经贸往来:国际清真食品中心的建设,马来西亚投资1亿林吉特建造清真公园;旅游业,海合会国家游客数量从2001至2007年持续增长100%;海合会国家加快在马来西亚开设伊斯兰银行的分支机构,沙特拉吉哈(Al-rajhi)银行和科威特金融公司(KFH)是其中最为知名的银行[22];服装业,马来西亚时装批发进出口商会总会长洪细弟就指出:大马时装业在“如今2010年,在面对零关税实行下,要冲出东盟国家,往中东国家发展”,“在零关税下,进口的原料便宜,制造后出口就会更有利,尤其是把时装出口到把大马视为回教国而没有征税的中东国家。”[23]
三、对中阿经贸合作关系的启示
选择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案例对于中阿经贸合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意义来自于东盟的构成、发展与中国的相似性。
首先,就东盟国家的构成来看,既有诸如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既有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天主教国家菲律宾,还有佛教国家泰国、缅甸,以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这与中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国幅员辽阔,既有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市,也有西部相对欠发达省区;中国民族众多,既有无神论者,也有大量的佛教徒和民间信仰者,还有“大聚居、小散居”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宗教文化背景呈多元化。
其次,从东盟的发展历程来看,东盟经历了政治军事组织向经济组织的转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吸收所有东南亚国家加入,并最终形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东盟内部实现了整合,为其开展整体的对外经贸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在民国初年陷入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力量为实现国家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改革开放30年则实现了大陆地区市场的统一,这为中国在新时期开展对外经贸合作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东盟与海合会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给中国的相关经验是: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相协调。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和宗教众多、幅员辽阔但地理生态环境迥异的大国,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模式及习俗有着很大的不同,尤其是中国西北穆斯林聚居省区在向阿拉伯国家出口清真食品和穆斯林服饰上有着巨大的潜力,但缺点是在中国内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上地处内陆,无论是西方投资还是阿拉伯国家投资都极为有限。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对于中国有着大量的粮食需求,中国粮食产区主要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区,阿拉伯国家石油产业投资往往在中国沿海地区。因此,中国在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时,要充分发挥各省区的自身优势,统筹兼顾,抓住中阿经贸关系核心内容的前提之下发挥地方政府的对阿交往,第一,尤其是要鼓励西北省区积极发挥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优势,积极做大相关食品和服装产业,并积极吸收阿拉伯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直接投资以提升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第二,其他省区的粮食出口要配合国家对阿经贸关系的大局,将粮食出口不是当作单纯的粮食问题来看待,而是要认识到其中隐含的中东石油资源涵义;第三,中央政府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西北省区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提升阿拉拉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也有助于推进中阿经贸合作的深化;第四,中央和发达省市要大力发展高新科技,尤其是油气科技,并将科技产品出口到阿拉伯国家或吸收阿拉伯国家对油气产业的直接投资;第五,要将具体阿拉伯国家区别对待,阿拉伯国家内部也存在着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中国应重点考虑油气资源丰富、资金雄厚的海合会国家作为经贸往来的对象;第六,中国与海合会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之中,可以发挥地方外交的作用,积极推进宁夏等省区先行与海合会之间减少关税,建立准自贸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其独特的民族和宗教优势、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应当起到西北地区重点发展对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领导作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发展对阿经贸合作时,要明确两点:第一,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只是吸引阿拉伯国家关注的表层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否能够提供对方需要的产品,如义乌模式的成功与伊斯兰背景无关。第二,要明确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经贸是中阿经贸合作中的一环,宁夏只有抓住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只面向阿拉伯国家而忽视国内市场是难以长久发展的。
总而言之,只有确立粮食和科技换石油的主线,中阿经贸合作关系才能得到健康发展,而在此过程之中,西北省区和发达省区之间要有中央指导下的战略分工,积极发挥自身在对阿经贸中的独特优势作用,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石油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实现和缩小西北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
[1] Rodney Wilson,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GCC and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in Hannah Carter,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Routledge Curzon, 2004, p.113.
[2] Ghazanfar Ali Khan, “GCC, ASEAN, Set Out Visions of Cooperation”, Arab News, April 22, 2007.
[3] “ASEAN-GCC to Elevate Relations to Regular Ministerial Meetings”, September 17, 2008, at http://www.aseansec.org/21950.htm.
[4] GAEC, “About Us”, at http://gccaec.com/index-1.html.
[5] GAEC, “Services”, at http://gccaec.com/index-3.html.
[6] ASEAN, “First ASEAN-GCC Ministerial Meeting”, June 30, 2009, at http://www.aseansec.org/PR-1st-ASEAN-GCC-MM.pdf.
[7] ASEAN, “Joint Pres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GCC Ministerial Meeting”, June 30, 2009, at http://www.aseansec.org/PR-JPS-1st-ASEAN-GCC.pdf.
[8] Petchanet Pratruangkrai, “Asean, GCC Likely to Start FTA Talks Soon”, The Nation, December 4, 2009.
[9] “AEM to Promote Greater Understanding with GCC & MERCOSUR”, Bernama, February 28, 2010.
[10] Ghazanfar Ali Khan, “Stronger GCC-ASEAN Ties Pledges”, MENAFN, April 12, 2010.
[11] Kenneth A. Reinert, Ramkishen S. Rajan,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the World Economy, Vol.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02.
[12] Petchanet Pratruangkrai, “ASEAN, GCC Likely to Start FTA Talks Soon”, Nation, December 4, 2009.
[13] Jumana Al Tamimi, “Singapore Wants Free Trade Pact for GCC and ASEAN”, Gulf News, March 23, 2010.
[14] Abdul Basit, “Malaysian Keen to Boost Business Ties with GCC”, MENAFN, April 14, 2010.
[15] 钮松:“‘手中无粮 心中发慌’的影响”,《新京报》2008年4月13日。
[16] 陈杰:“试析阿拉伯粮食安全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2期。
[17] Shuchita Kapur, “Fresh Water Infrastructure Vital for GCC”, Emirates Business 24/7, 2009-11-05.
[18] Frederik Richter, “GCC, ASEAN Eye New Trade Bloc Based on Food, Oil”, Arabian Business, 2009-06-30.
[19] “Middle East Needs More Vietnam Workers”, 2008-01-18, at http://english.vietnamnet.vn/social/2008/01/764782/.
[20] Joe Avancena, “GCC, Philippines, Launch Economic Cooperation”, Saudi Gazette, 2009-06-13.
[21] Asmak Binti Ab Rahman, Mohd Fauzi Bin Abu-Hussin, “GCC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Malaysian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Vol.2, Fall 2009, p.50.
[22] Ibid., pp.52-53.
[23] “零关税:零关税·物品会降价吗?”,《星洲日报》2010-01-06。